|
《真正的归宿:和米歇尔·波尔特的对谈》是安妮·埃尔诺的谈话集,在这本书中,安妮·埃尔诺讲述了她的女性主义观点、最初的创作动机、真切的生命体验与自己的文学观。本文经出版社授权,选自《真正的归宿:和米歇尔·波尔特的对谈》,由知名法语文学科研者、译者黄荭翻译。
原文作者
丨[法]安妮·埃尔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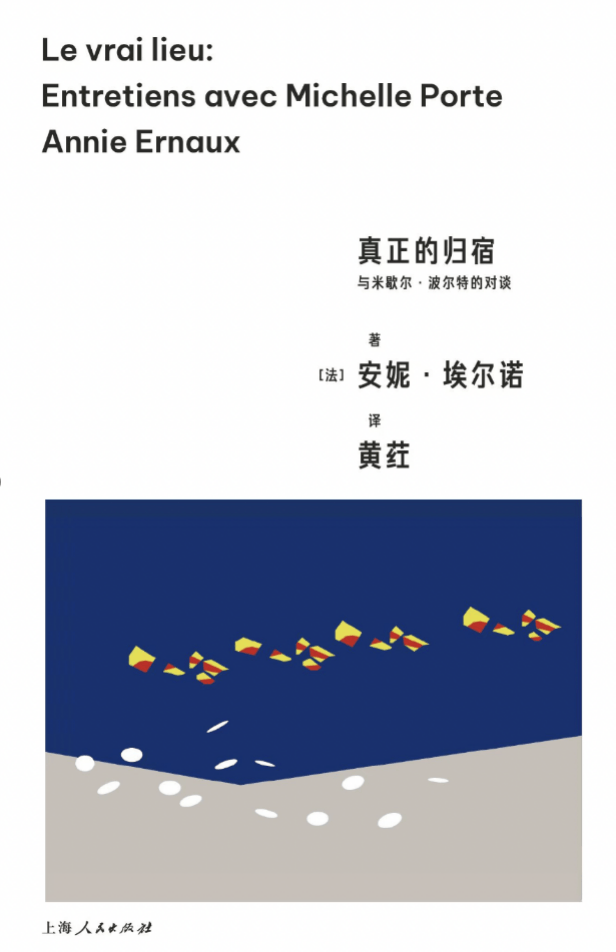
《真正的归宿:和米歇尔·波尔特的对谈》,作者: [法]安妮·埃尔诺,译者: 黄荭,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4年8月即将出版。
我不是写作的女性,
我是写作的人
安妮·埃尔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女性的身份到底寓意着什么。由于我写作时无这种身份焦虑。由于总被打回到这个问题是痛苦的根源,是反抗的根源。女性总是被打回到女性身份这个问题,为了守护人们欠好意思承认的男性的主导地位。与生活在1950年代的女性相比,即使是生活在2000年代的女性,亦始终忍受着这一状况,男性主导的现象乃至在文化行业亦在所难免。女性革命无出现过,它始终都有待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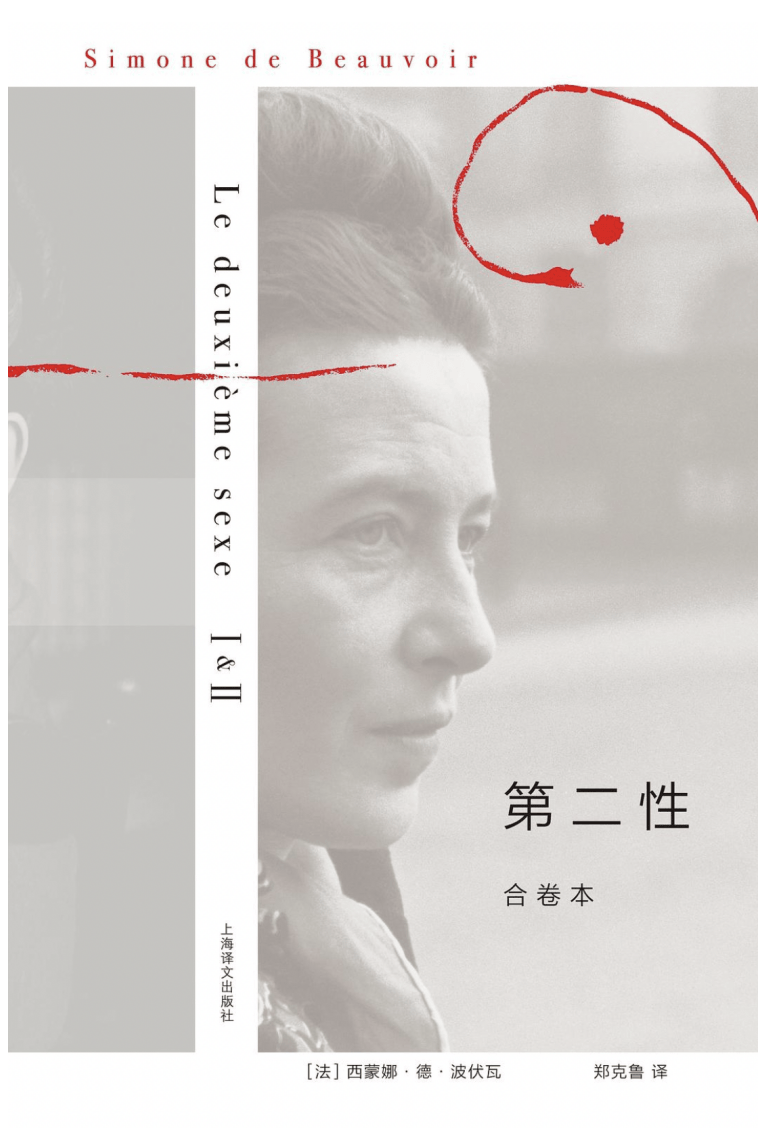
《第二性》,作者: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译者: 郑克鲁,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4年1月。
在女性主义行业,我的第1个典范是我母亲。她以自己的方式抚养我成长,以自己的方式处世,以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让任何人强加给她任何东西。她从来不要我分担家务,从来不要。亦无让我在店里帮忙。仅仅是我从15、16岁起始才要整理自己的床铺!我所有的时间都能够用来学习、玩耍和阅读。我能够随时阅读,想读多少就读多少。无课的早晨,我会躺在床上看书看到晌午。我记得我在课堂上炫耀这个特权时,老师用一种骇人的严厉眼神看着我。无疑床和阅读联系在一块对她来讲有些不正常、不健康……
我在18岁那年读了西蒙·德·波伏瓦的书。先是《一个规矩女子的回忆》(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这本书并无尤其打动我。它讲述的是一个在优越环境中度过的童年,与我的童年大相径庭,无任何交集。之后是《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这是一次真正的觉醒。但那时候,我并无将自己所受的非典型教育与波伏瓦写的东西联系起来,亦便是说,我抛开了自己所受的教育,而不是对其进行审视。我一头扎进了一个巨大的、到那时为止对我而言还是未知的行业,那便是女性的历史和女性的处境。直到1970年代,随着女性运动的兴起,我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多么不传统,并因此呢对母亲心存感恩。
我认为我所接受的教育和《第二性》的双重影响,让我不受1968年后盛行的一种特指的女性文学的影响。我曾读到亦听到过,要用你的身体,你女性的身体去写作。当我起始写作时,我并不觉得是在用我的皮肤、乳房和子宫去写作,而是在用我的头脑,用我的认识、记忆和抗争的文字去写作!是的,我从未这般想过,我是一个写作的女性。由于我不是一个写作的女性,我只是一个写作的人罢了。然则我有一个女性的故事,它与男人的故事区别,在避孕和堕胎自由之前,是最糟糕的被生育裹挟的故事。女性对世界的平常体验与男性并不相同。事实上,女性的困难就在于让公众认可她描述自己女性经历的合法性,尽管我自己并无受影响。何况哪些得到认可、被教授的文学作品95%是由于男性创作的,所推崇的典范亦大大都是男性,乃至在今天,与男性经历关联的写作题材,例如战争、游历等,仍受到极度注重,而哪些女性特有的经历,例如生育,却向来鲜少得到关注。
我的书是按照我做为女性的经历写就的,《冻住的女性》和《事件》,在它们出版伊始要么受到冷眼要么反响平平。仿佛这些作品的写作风格、行文手法因其主题而变得何足道哉了。仿佛它拉低了我的文学表达。
然而在我看来,写作手法的差异更大都是由社会阶层决定的,而非性别。不论是男人还是女性,其写作手法都是由于阶层出身决定的。出身普通阶层的人和出身上流阶层的人运用的写作手法是区别的。这无疑是写作最重要的底色。

《一个规矩女子的回忆》,作者: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译者: 罗国林,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3年2月。
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中有些让人非常不舒服的地区。一切似乎都显示,所有女性都面临着相同的处境,仿佛资产阶级出身的女性和工人、农民阶级出身的女性之间无区别。好吧,男性统治的确贯穿了全社会、各样社会阶层。但确切地说,区别的社会阶层受到男性统治的程度是区别的。我觉得在受过资产阶级高等教育的女性,例如我的婆婆,和我小时候身边的女性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她们无相同的身体,亦无相同的经历。这种不平等在我那段艰难痛苦的堕胎经历中变得格外显著,那时的我无钱亦无关系,费尽周折地寻找堕胎途径,而与此同期,有钱人家的姑娘却能顺利地去瑞士堕胎,在那里堕胎是合法的。
米歇尔·波尔特:您是怎样有了写作的念头呢?
安妮·埃尔诺:我当时19岁,我的生活很糟糕。高中毕业后,我进入师范学校的职业培训班学习。我不想再依靠父母了。我非常巴望自由。我觉得西蒙娜·德·波伏瓦或多或少促成为了我的这种巴望,而作为一名教师似乎是快速得到自由的途径。然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我没法忍受师范学校的寄宿制和它的认识形态,我尤其懊悔可能再亦无机会继续文学高等教育。我走得很忽然,半途辍学,背弃了我对国家教育系统的承诺,当然,是在我母亲首肯之下。一月后,我已然到了英国,在伦敦郊区芬奇利(Finchley)的一户人家做互惠生。我感到非常空虚,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早上我做家务活,下午则无所事事。我无学习英语,而是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只阅读当代法国文学作品。芬奇利的公共图书馆里有一个法语书籍区,“新小说派”的书非常多,我当时对它还是一无所知。我不记得自己确切是从何时起,又是怎样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由于就像我说的那样,我当年写的日记已然不复存在了。只记得8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我在西芬奇利的一个公园里起始写作。10月,我回到法国,计划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我最终晓得自己应该做什么了。我要经过学习文学作为一名法语教师,但这不是我的首要目的。我要作为一名作家,“留在”文学行业。这两年时间里,我仍然巴望写作,但我必要先经过考试,拿到奖学金。为了取得文学“学位证”,我必须学习语法和语文学、外国文学和历史等繁重的课程。大学前两年写的有些小说的开头,已然无迹可寻。直到大学三年级,我才完成为了一部小说,篇幅很短,文案重概念,且晦涩难懂,可能在读者看来怪里怪气的。我把它寄给了瑟伊出版社的手稿部。我从未想过要去见一位作家,乃至从未想过要把我的小说寄给他。那是一个遥远的巴黎世界。瑟伊出版社的让·凯罗尔(Jean Cayrol)回复了我,他非常友善。他说,从整体上看,我的写作特别有野心,但我还无找到实现它的办法。我以自己当时的世界观为基本打造了我的文本结构。要晓得,自我的现实性并不存在于意象之外,哪些过去的意象,即童年的画面,人们对当下的印象,以及所有对将来的想象。最后,是《悠悠岁月》,还有哪些照片所描绘的女子的思想,将实现我在第1个文本中未能企及的目的。
让·凯罗尔的拒稿并无让我气馁。我真的下定决心重新起始。但就在那时,我做为女性的故事显现了,亦是所有女性的故事。身为女性,我遇到了所有可能阻碍我重新起始写作的阻碍。当然你能够说,就像人们以前常说的,那是我的错。为何,的确,为何要做爱并弄大了肚子?不,这不是女性的错,只是社会的错,当时社会无为女性供给任何处理方法,从而实质上阻碍了女性的自由。我直面了我从未想象过的“命运”,不想怀孕却怀孕了。首要是堕胎,而后是“被迫”的闪婚,以及不想但最后接受了,乃至是愉快的分娩。我的文凭是在最糟糕的要求下取得的。我的教师职业生涯的开端亦是如此,国家教育分部从未采取过办法改善教师的工作要求。我被安排到离家40千米的地区工作,冬天上班路上会积雪。所有这些经历后来都被我写进了《冻住的女性》。
我记得暑假儿子午睡的时候,我曾尝试写作,但总有种种干扰。另外,我亦无勇气把写作的欲望放在首位,由于这与家人对我的需求相比显出微不足道,而我认为自己没法回避这些需求:带孩儿、谋生……让丈夫一块分担家务是非分之想。这不被社会所接受,我乃至连想都不敢想。那是在1968年前夕,而这种传统秩序只是女性史前史的冰山一角。
我想是一个突发的变故,父亲的逝去,改变了我写作的欲望。我带着小儿子回伊沃托,准备陪父母待1星期,结果次日父亲就突发心梗,三天就去世了。时迄今日,我仍觉得父亲的死就像是一场地震,一个转折。思绪翻滚。我明白了是什么让我和父亲渐行渐远,而这是无可挽回的。我认识到这是一场社会适应,就我的状况而言非常成功,由于我爷爷不识字,我父亲在农场干过活儿,后来当了工人,再后来成为了咖啡店老板,而我却刚被录取为语文老师。我陷入了和父亲天人永隔的伤痛中,从此我再无机会作出弥补。从那之后,我再也不用前几年的方式写作了,我要写有些在当时我还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很久以后,社会学告诉我,我这种状况属于“阶级变节者”。我都不晓得在1960年代末这个词是不是已然存在。
当老师对我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不是它赋予了我重新写作的欲望,而是唤醒了深埋在我心底的东西。在父亲死后的第1年,我负责给初一的孩儿上所说的“实践”课,为她们的职业技能考试做准备。我逐步认识到,尽管一起始我并不想承认,这些学生身上有我的影子,又或说我身上有她们的影子。在我接受高等教育的这些年里,我忘了自己从小成长的阶级,忘却了自己少女时期12岁、15岁时的样子。转眼间,我和一群儿童和青少年相处,她们迫使我思考有些我以前从未问过自己的问题,在任何地区都不会问的问题。这些生活在主流文化之外的青少年,她们的父母不读书,亦不带自己的孩儿去剧院。我怎样才可把我认为美好的事物传达给这些孩儿,并让她们对此产生热爱?从这群青少年的举止行径和言语中,我敏锐地认识到她们所处的环境与受过教育的世界之间存在鸿沟,而我已然成为了受过教育的世界的化身,亦是帮忙她们实现阶级跨越的“传送带”。而她们,她们还处在我出身的环境里。我扪心自问:我在这儿教授的东西,最后对她们有什么影响?由于受到所处环境的局限,她们大都数人一眼便看到了自己的此刻和将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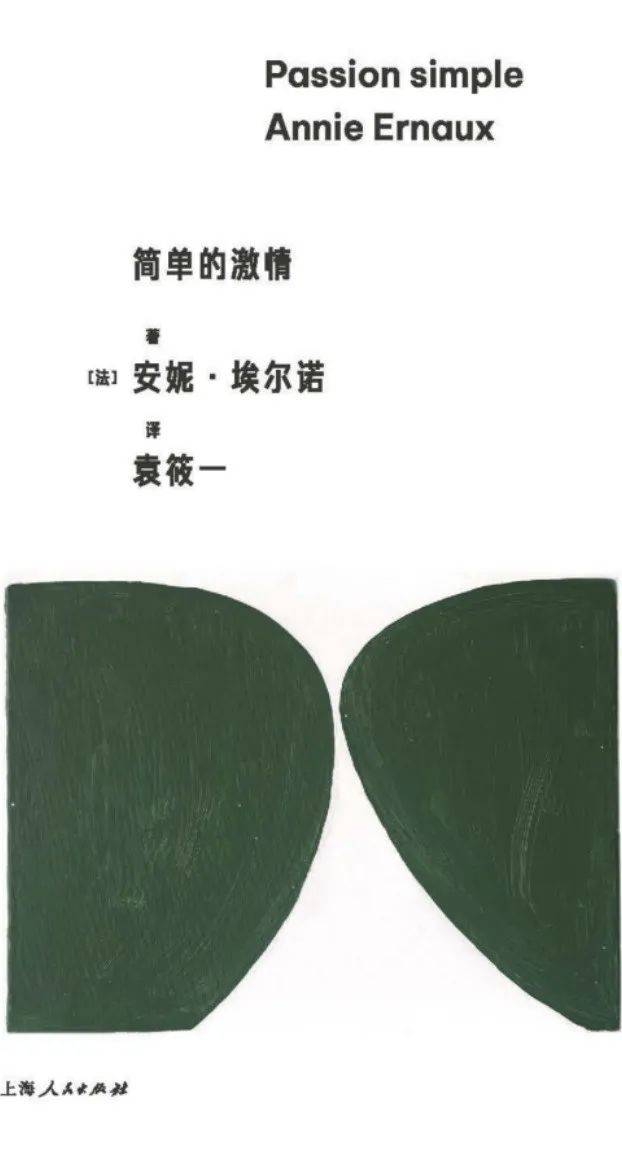
《简单的激情》,作者: [法]安妮·埃尔诺,译者: 袁筱一,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3年7月。
轻飘飘地说一句“不是所有人都有一样的机会”,和在法语课堂上亲身见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始终问自己,为何会这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要把这些都写出来实在是太沉重,太困难了。我必须有许多的时间才行。而后,到了1970年代初,把这些都写出来成为了我独一要做的事情。我要说的便是《空衣橱》,这本书是回归本原,回到哪些或许决定了我一辈子的事情。它们决定了我的世界观,亦决定了我写作的内视角。我出生的这个世界与我经过学习而抵达的世界截然区别。我的祖父母都是农民,但要重视,她们是那种无土地的佃农,她们耕种的是别人的土地。我父母,她们的家庭、顾客、以及咱们周边的人都出身工人阶级。当然了,我父母她们自己亦是工人,顶多算小商贩。她们说自己始终都活得忧心忡忡,始终都在害怕会“重新沦为工人”。然则事实上,她们的这种恐惧比这个还要严重,这是一种根深蒂固、发自内心的恐惧,是一种对自己局限性的坚信。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无相同的社会风气、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这种震撼始终伴同着我。乃至是身体上的。有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不,不是因为害羞或不自在。而是由于位置。仿佛我不在真正属于我的位置上,仿佛我人在那里,但心却无处安顿。
大都数时候是在有些社交场合。在这些场合,我不得不和有些人打交道,而这些人她们本身就在某些程度上否定了我最初的那个世界,亦便是被统治者的世界。她们不属于那个世界,便是这般。
有一个地区,在那里,上面说到的种种都不存在,那便是写作。是的,写作是一个地区,它是一个精神之地。虽然我不是一个写虚幻故事的作家,我写的是记忆与现实,但这对我亦是一种逃离。让我“在别处”。始终败兴,写作给我的印象便是沉浸。沉浸在一个并不属于我的现实之中。然则这般的现实却是由于我创造的。我的经历是一种跨越的经历,一种和社会阶层分离的经历。这种分离在现实中存在,是空间的分离,教育体制的分离。有些孩儿16岁就辍学了,可她们才懂这么一点点东西,而另有些孩儿呢,她们就会继续学业直到25岁。社会阶层的区隔与我所经历的区隔之间有一个一起点,一种巧合,这使得写作让我感兴趣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是去探究这种区隔产生的机制。
时间的流逝
米歇尔·波尔特:安妮,在《悠悠岁月》这本书中,您将一名女性的私密生活、您的生活、时代以及战后变迁这些元素都很好地融合在一块。
安妮·埃尔诺:大约在40岁上下,当我回想自己的一辈子时,我惊讶地发掘,从战后到1980年代,世界和法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我要写的这本书便是关于这一点,关于时间的流逝,关于我自己和外面的世界。最起始的时候,书中触及的时间是三十五年,但随着我写作时间的延长,书中描写的时间亦越来越长。当我真正动笔写的时候,五十数年的法国生活等着我去书写。况且是用我对时间的记忆、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记忆去书写。由于咱们不会仅仅只记得自己。咱们是在特定的情境、特定的环境中记住自己的。咱们会记得自己与有些人、有些歌、有些物品一块在特定场景里,这些都记录了时间的流逝。我想,倘若区别时挽回从战后我有认识的那一刻起始直到此刻所出现的一切,我就没法挽回我生命中某些东西——当然不可能挽回所有一切。那个此刻最后定格在2007年,我写完这本书的那一年。
去探究对咱们这一代人来讲过去五十年间世界出现了怎么样非同寻常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的挑战。1950年代初,生活方式与我父母乃至祖父母辈的没什么区别。在某种程度上,那时的咱们还过着和战前同样的生活。倘若咱们从城市以及房屋内部进行比较,1950年和2000年之间的差异肯定大于1850年和1950年之间的差异。变化不仅表现在事物上,还表现在咱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上。乃至咱们对将来的憧憬亦出现了变化。
从历史的方向来看,我只是将自己摆在一个被历史潮流所裹挟的普通人的视角,对历史事件可能会有的记忆。而绝非历史学家对戴高乐、密特朗抑或是1968年五月风暴的记忆。我要做的,是在个人记忆中重现集体记忆。描写历史进程在咱们身上留下的痕迹。这种进程永远不会停止。2007年,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认识到我仅仅是中断了写作的过程,而这个世界仍在运转。因此呢,从这本书里走出来的时候,我有点伤感。我不打算给这本书写续篇。一本书是一个封闭的整体,无后续之说。
《悠悠岁月》,作者: [法]安妮·埃尔诺,译者: 吴岳添,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1年6月。
在《悠悠岁月》中,个体——“她”“咱们”——与社会持续地彼此交融。我能够肯定的一点是,咱们并不是或多或少经过语言与他人交流的孤立个体。他人常常以这般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于咱们身上。例如教育的传承,抑或是流行于某个时代、在咱们身上留下印记的所有一切,不管咱们处在什么年龄。在我10岁的时候,他人所经历的过去——尤其是1939年至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经过别人的叙述以及我自己亲眼目睹过的轰炸和废墟的照片深深刻入了我的脑海。20世纪初人们的生活、人民阵线,这一切我都无亲眼见过,但关于这些事情的叙述让我对那个时代形成为了一种想象中的记忆。那是一段被感知的时光,是1950年代到2000年的世界留在一个女性记忆中的印象,《悠悠岁月》就取材于此。由于无论是时间还是记忆都不会停滞不前,因此它采用了一种连贯的、流动的叙述。于我而言,重要的传达这种流动性,它始于1950年代,那时一切都很慢,人们习惯沉默,轿车、电视亦很罕见。这种流动无间断地延伸迄今——由于它不存在完全的中断,即使在1968年亦是如此——始终延伸到咱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消费与富足的时代。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但它仍是咱们生活的背景。
在我看来,一样重要的,是把握住将来的变化,把握住咱们对将来的总体期望。在1950和1960年代,青年人是将来的化身,她们的存在本身便是将来的形象。但青年一代所表率的炽热、好奇乃至期盼逐步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广泛的衰老、谨小慎微,乃至是一种非常剧烈的、与日俱增的对他者的恐惧。害怕陌生人。历史书、电视上的文献纪录片与对近十年时光的描绘,这其中所呈现的时间并非个体的历史。完全不是。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与时代有些脱节,我亦想展示这一点,即咱们怎样能在完全融入当下社会的同期以区别于主流观点的方式进行思考。没有形容词去修饰《岁月》[《悠悠岁月》的法文书名是《岁月》(Les Années)。——译者注]寓意着人们不可定义这段过去的岁月,同期它亦是没法被定义的。仅有在岁月中持续向前、持续被覆盖的存在。哪些属于我的时光,属于其他人的时光。
我想写的不是一本历史书,乃至不是一部回忆录,我想做的便是原本来本的还原过去,还原出它还是“此刻”的样子,换句话说,只是一种感受。是人们在五月风暴的前一月所感觉到的。显然,当时人们什么都没察觉。而这种毫无察觉本身就很重要。正是带着对接踵而至的“此刻”的感受的记忆,我才写出了《悠悠岁月》。说实话,这本书完全是凭着对各样感受的记忆写就的。
米歇尔·波尔特:阅读《悠悠岁月》时,咱们认识到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此之快,从过去的匮乏到今天的过剩。
安妮·埃尔诺:1960年代之前,人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相对匮乏的世界。什么都短缺,食品、衣服、各样物品。什么都舍不得扔,无论是面包还是破了洞的袜子,长筒袜缝缝补补后继续穿。什么都“有用”。生活方式和道德风尚的选取亦很少。我感到我的童年是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度过的。语言亦不丰富,仅有宗教用语、学校用语和广播用语。从1970年代起,一切都爆发式增长,咱们进入了一个杂乱过剩的世界,亦便是说,咱们难以理解变化的事物和行径。但我的写作计划并不是描绘一幅悲观的画卷,这种变迁并不令我难过,倘若说有什么事情是我认为没法想象的,那便是回到过去。亦许在《悠悠岁月》的结尾并无预示美好的将来。但就算“美好的将来”这一说法,一样亦是属于过去的。
要晓得,咱们的思考离不开话语。可我不爱好今天咱们用来思考世界的话语,那是消费主义的话语、自由主义的话语。同期亦是排斥哪些刚进入法国社会的新移民的话语,为了赶走她们。人们谈论新城,之后是街区,还有有些敏锐区域。这些都是为了产生区别的话语。就在咱们交流的时候,我确实在担心,是的,担心社会整体心理的变化。好吧,我要说出这个词,一个我始终回避的词,特性,我担心它渗透到认识中,渗透到语言中,担心显现一种倒退。法兰西特性。我不晓得它寓意着什么,特性。当然,咱们运用法语,咱们亦持有法国记忆,由于咱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一样的事情,但不包含法兰西特性。
毫无疑问,过去的二十年里,社会不公加剧了、生活方式的差距拉大了、青年人的期待亦越来越不同样。青年人是在第三个千年开局之际最大的受害者。她们自己并无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只谈论老年人。衰老是人生的最后一个周期,但人生最初的周期呢?难道不是至关重要的吗?教育,学习,有机会步入社会、找到一份不仅能谋生(但乃至这个亦不可得到保证)的工作,所有这些才是问题所在。对青年人寄望不多,她们自己亦不抱什么期盼。1968年后,在全部1970年代,青年人让人害怕,让戴高乐政府害怕,亦让这段内忧外患时期的内政部长马塞林[ 马塞林(Raymond Marcellin,1914-2004):1968年五月风暴时的法国内政部长。——译者注]害怕。但最少这证明青年一代是存在的。而此刻,似乎青年一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存在了。这个社会无它的位置了。
如今,中学的首要任务是安全。守护权威、发扬传统、追求卓越,仿佛仅有那小部分在市中心上学的青年人才是成功教育的标杆。工人阶级的孩儿逐步被淘汰出教育系统,这种现象从未停止,然而除了对此感到惋惜之外,从未有人想过改变这个局面。
去年,我到塞尔吉中学给经济和社会科学的高二学生上课,那是一个混合班,学生们来自区别的民族。那儿青年人对学习的巴望和热爱令我动容。她们提了有些很中肯的问题,而后写出有些当下非常有趣的“见闻”。这些高二的学生和曾经的我同样,都是社会阶级的“变节者”,然则她们今后的旅程会比我更艰辛。她们会得到高中毕业文凭,或许还会继续学习深造,但最后她们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社会对这些移民出身的青年人有着不明说却真实存在的卑视。在1950和1960年代,倘若你是农民、工人或小商贩的孩儿,想要经过教育取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针对外来移民的孩儿来讲,更加是难上加难。政府已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把教育当作重中之重了。
真正的归宿
米歇尔·波尔特:听您说话,我不晓得您对当今世界的看法是悲观的还是阳光的……
安妮·埃尔诺:“阳光”和“悲观”这两个词都是问卷调查用语,在我的眼里,它们无任何实质含义。独一重要的问题,是“咱们要怎么办?”。当然,咱们能够听之任之,逆来顺受,或享受这个世界,这都是唯美主义者的观点,享受只属于咱们自己的小小的幸福,照顾好这世上属于咱们自己的小角落,这就足够了。像这般,咱们就能过得很好,或许吧,然则我不想这么活,亦不想让我爱的人们这么活。更确切的说,咱们要扪心自问:咱们能改变什么?虽然咱们很清楚,改变从来都不是从零起始,咱们应当摈弃彻底决裂的想法。
米歇尔·波尔特:那您觉得应当怎么做呢?
《一个男人的位置》,作者: [法]安妮·埃尔诺,译者: 郭玉梅,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2年10月。
安妮·埃尔诺:就我而言,除了写作之外,我确实想不到别的事情。我始终觉得,写作便是介入世事。然则要怎样介入呢?肯定不是靠写有些激进的文案。在我看来,我必要从哪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境遇出发,就例如说当我看到一把刀,不由自主我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总是刺得更深,把伤口弄得更大。我始终反对将我的小说看作是一种自我虚构,由于自我虚构这个概念本身就有一种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寓意。我从不期盼把这本书当作是个人的东西。我创作,不是由于我经历了某些事情,而是由于这些事情在他人身上亦出现过,我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在《羞耻》《一个男人的位置》《简单的激情》这些书中,我想要强调的不是这些经历的特殊性,而是它们没法言说的广泛性。当没法言说的东西变成文字,它便拥有了政治性。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谁都不会替你生活。但你不可把它写成仅仅是你自己的经历。哪些经历必要是跨人叫作的,超越个体的,正是如此。仅有这般你才可探索自我,用区别的方式生活,并为之感到高兴。文学能够给人带来愉快。
话说回来,我压根不晓得我的书是怎么产生功效的。然则,倘若无这种想要我的书变得有用的念头的话,我就没法写作。
介入世界是为了改变世界,一旦带有这种目的,就和写作的对象与“主题”都无什么关系——尽管它们亦是介入的一部分,但毕竟选取写轻轨上的乘客,还是写卢森堡公园的漫步者,这两者的道理还是不同样。这是写作要采用的形式问题。在起始写《空衣橱》的时候,我一下就明白了这个问题。写作必要传达出那种经过教育和羞耻施加在叙事者德妮丝身上的漫长又不可见的暴力。因此咱们必须用语言的暴力来回应这种文化统治下的无声暴力。对那时的我来讲,介入世界便是经过重新找回原始语言的力量和“卑鄙”,来揭示社会阶级之间的鸿沟。
我花了更加多时间来确定《一个男人的位置》的写作形式,这种对事物不加评论的描写方式,说到底,触及的是内在的暴力,而再也不是《空衣橱》中展露在外的暴力,我认为经过只摆事实而不加评论的创作手法展现的这种内在的暴力更拥有冲击力。当我写这本关于我父亲的书时,我重看了《大路》[ 《大路》(La strada)是1954年由费德里科·费里尼导演的一部影片。],我最巴望达到的便是这种简洁的风格,一切情感都在不言中。
《大路》剧照。
正是写作的形式颠覆了一切,让咱们用区别的方式去看事物。旧的、既定的形式已然没法再让咱们以新的方式观察事物。1950和1960年代,有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启发,一种毫无探索精神的文学,例如安德烈·斯蒂(André Stil),因此呢亦注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在《重现的时光》的结尾,普鲁斯特写道,就像埃尔斯蒂尔(Elstir)之于夏尔丹(Chardin),“我们仅有放弃自己心爱之物,才可有朝一日重新持有它”。咱们必要用和咱们所崇拜的作家区别的方式去写作。
显然,咱们从自己发掘写作的独特之处。在改变传统的同期,咱们亦脱胎于过去的文学。我晓得我并无和前人的文学完全割裂,这是不可能的。我是文学史的继承人。在1960年代我起始写作时,我就投入到了新小说的浪潮中。1970年代,女权运动作为了一大推力,并激发人们书写自我,尽管当时我并无真正参与其中。写作并非一种能够神奇地和其他事情截然掰开的活动。写作的时候是完全孤独的状态,但它和时代、和其他写作者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联系。然则,当你写得越多,你就越不会受到其他作家写作的影响。
此刻,我好似在挖同一个坑。我感觉我的书彼此是区别的,但又有什么东西将它们联系在一块。做为作者,我所处的位置未必最能看清到底是什么把它们联系在一块,我的书到底怎么样。乃至不方便去谈论它们!有一天,在布拉格,一次讲座结束时,我无意中听到邀请我的文化参赞的话。他说:“她基本不晓得怎样谈论她自己的书。”或许他是对的,对我而言,谈论自己的书很难,尤其为了让它们被更加多人接受。谈论写作对我寓意着什么,这个专题或许我更善于。由于,倘若我被逼到无言以对,那毕竟是我感觉最能发挥自己所长的地区。写作,才是我真正的归宿。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法]安妮·埃尔诺;翻译:黄荭;摘编:王铭博 张婷;导语校对:杨利。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伴侣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宣传。返回外链论坛:www.fok120.com,查看更加多
责任编辑:网友投稿
|